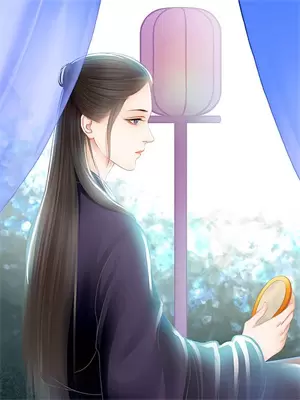我从小在城里长大,却对乡下有种说不清的向往。不是想看什么青山绿水,
就是图个能撒开脚丫子疯跑的“野”劲儿。城里的楼房密密麻麻像鸽子笼,
想跑两步都得小心翼翼看着路,生怕撞着人或者踩着啥,可乡下不一样,那田埂无边无际,
踩上去软乎乎的,就算在上面打滚翻跟头,也没人管你,那种自在,
是城里孩子想都想不到的。差不多每隔三四个月,爸妈工作不忙了,
就会抽空带着我回乡下大伯家住几天。大伯家在村子西头,有个挺大的院子,
院里种着两棵有些年岁的老槐树,枝干虬结,一到夏天,叶子密得能把大半个院子都遮住,
留下好大一片阴凉。每次我们的车刚开到村口,总能围上来几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娃子,
领头的往往是二柱。他们一个个皮肤晒得黝黑发亮,光着脚丫子,裤腿卷到膝盖上面,
小腿和脚背上沾满了干涸的泥点子,活像刚从泥地里钻出来的泥鳅。
他们从不嫌弃我穿得干净整齐,一看我下车,就热络地拉着我的手,
嚷嚷着带我去田里找好玩的,不是逮蚂蚱就是挖泥鳅,
要不就是去摘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果子。通常不到半天功夫,我就能跟他们混成一个样儿,
衣服上、脸上、胳膊上全是泥道道,爸妈见了也只是笑着摇摇头,
说我“一回乡下就野得没边了”。那年我刚好八岁,放暑假的时候,又跟着爸妈去了大伯家。
和往常一样,车刚在村口停稳,二柱、狗蛋他们几个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,
呼啦啦地围了上来。二柱比我大两岁,是这帮孩子的头儿,他跑得最快,胆子也最大,
哪片林子里的野果最甜,哪块水田里的泥鳅最肥,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我们一群孩子吵吵嚷嚷地就往村东头的那片稻田跑去,那边的田埂比较宽,水也浅,
最适合我们这群孩子追逐打闹。刚跑到田边,还没等我们开始今天的“工程”,
我就眼尖地瞥见田埂那头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。那是个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,
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、几乎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粗布褂子,
肩膀和手肘处还能看到细密的补丁。他的头发乱糟糟的,像是很久没梳理过,
上面甚至还沾着几根枯黄的草叶和干涸的泥屑。他的脸长得其实挺周正,眼睛尤其大,
睫毛长长的,可那眼神却直勾勾的,没什么神采,显得有点呆滞。但不知为什么,
那呆滞里又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诡异——他那双眼睛太亮了,黑眼仁像浸在清水里的玻璃球,
异常清澈,却又没什么温度,看久了让人心里有点发毛。“哎,你是谁啊?哪个村的?
咋从没见过你?”二柱胆子大,率先朝着那边喊了一嗓子,
他手里还捏着刚才路上逮到的一只绿油油的大蚂蚱,蚂蚱的后腿还在徒劳地蹬动着。
那孩子像是没听见一样,依旧站在原地,一声不吭,只是微微转动着眼珠,
木然地看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。他的嘴角平平地抿着,看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,
整张脸没什么表情,皮肤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白,隐隐透着点青灰色,像是很久没见过太阳,
又像是……刚从冷水里捞出来一样,带着一股子湿漉漉的寒气。狗蛋是个急性子,
见他不回答,便凑了过去,伸手想拍一下他的肩膀:“喂,问你话呢!哑巴啦?
”可他的手刚碰到那孩子肩头的粗布褂子,就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似的,猛地缩了回来,
脸上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,扭头对我们小声叫道:“妈呀!他……他身上咋这么凉?
跟……跟刚从那河里爬出来似的!”那孩子对狗蛋的反应依旧无动于衷,他没有躲闪,
也没有任何表示,只是慢慢地、有些僵硬地挪动脚步,悄无声息地跟在了我们这群人后面。
我心里莫名地“咯噔”一下,下意识地就低头去看他的脚。我们都穿着塑料凉鞋或者布鞋,
鞋底沾满了田埂上的湿泥,每走一步,都会在比较干的地方留下一个清晰的泥脚印。
可是他的脚上……好像也没穿鞋,就那么光着,踩在湿软的泥地上,居然一个印子都没留下!
田埂上的泥土湿滑,我们走过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坑洼,可他走过的地方,泥土平整如初,
仿佛什么都没有踩踏过一样。二柱撇了撇嘴,有些不以为意:“估计真是个哑巴,
听不懂话吧?没劲。”我们这群孩子正是贪玩好动的时候,见他不说话,反应又迟钝,
起初的新奇感很快就过去了,也没太把他当回事,继续着我们自己的游戏。一开始,
我们还尝试着跟他交流,把逮到的蚂蚱递到他眼前,或者指着泥鳅给他看,
可他要么愣愣地没反应,要么就是慢半拍地做出相反的动作。给他蚂蚱,
他接过去就死死攥在手心里,直到那蚂蚱被他捏得不动弹了,或者挣扎着蹦走了,
他也只是眨巴一下那双过于明亮却无神的大眼睛,眼神依旧直勾勾地不知道在看哪里。
更让人觉得不对劲的是,他好像完全不怕头顶上那毒辣辣的日头。那天中午太阳特别猛,
明晃晃地挂在天上,烤得人皮肤发烫。我们玩累了,一个个汗流浃背,脸蛋通红,
都争先恐后地跑到田边那棵大槐树的树荫下乘凉,拿着草帽不停地扇风。可那个哑童,
却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毫无遮挡的太阳地里,毒辣的阳光直直地照在他身上,
足足晒了有半个多钟头,他的脸上、脖子上,竟然看不到一滴汗珠,
皮肤还是那种瘆人的青白色,仿佛太阳的热量根本无法穿透他那层冰冷的皮肤。“不对劲,
这娃邪门得很。”二柱悄悄把我拉到一边,压低声音说,他的眉头皱得紧紧的,“你发现没?
他晒了这么久,一滴汗都不流!还有,他走路咋一点声音都没有?跟个猫似的!
”被他这么一提醒,我赶紧竖起耳朵仔细听。我们跑跳打闹的时候,
脚步声、喘气声、泥块被踢落水里的“噗通”声,混杂在一起,热闹得很。可那个哑童,
明明就跟在我们身后不远处,却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,连最轻微的呼吸声都听不见。
他走路的样子也很怪,轻飘飘的,腿好像不怎么打弯,与其说是走,不如说是在平滑地移动,
像个……没有重量的影子。“别管他了,”我心里开始一阵阵发毛,
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感慢慢爬了上来,拉着二柱和其他小伙伴就往田埂的另一头走,
“咱们去那边挖红薯吃,离他远点儿。”我们在红薯地里忙活的时候,
他就安安静静地站在田埂上,面朝着我们的方向,一动不动地看着,
那双过于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,视线仿佛黏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互相扔着小泥块打闹,
有泥块不小心砸到他身上,他既不躲闪,也不生气,
只是任由那湿泥块顺着他的粗布褂子滑落到地上。奇怪的是,那泥渍沾到他衣服上,
很快就像是渗了进去一样,慢慢变淡,最后竟然消失不见了,褂子上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
我们坐在田埂上,啃着刚刚挖出来、简单用溪水冲洗过的生红薯,
把剥下来的红薯皮随手扔在地上。他也学着我们的样子,慢吞吞地弯腰捡起一块红薯皮,
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,然后又放到嘴边,用嘴唇碰了碰,随即又面无表情地放下了。
从始至终,他脸上都没有露出过一丝一毫的笑容,也没有发出过任何一点点声音,
安静得可怕。可我总觉得,他那直勾勾的眼神里,似乎藏着某种情绪,
说不清是羡慕我们玩闹的开心,还是因为他自己无法融入而感到的难过,
那种复杂难辨的东西,让我后背一阵阵发凉,总忍不住想回头看看他还在不在原地。
一直玩到日头开始偏西,天色渐渐染上了橙黄,大伯家房顶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的炊烟,
饭菜的香味似乎都能随风飘到田边了。二柱拍了拍身上的泥土,对我们说:“差不多了,
该回家吃饭了,明天再接着玩!”孩子们一听,立刻一哄而散,各自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跑去。
我家大伯家在村西头,回去要穿过一条窄长的泥土路,路两边是长得比人还高的玉米地,
密密麻麻的。风一吹过,玉米叶子就互相摩擦,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响声,
那声音听起来没来由地让人心慌,总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躲在玉米地里,
正贴着地皮悄悄地喘气。我一个人走在路上,脚下的土路被太阳晒了大半天,表面有点硬,
踩上去会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轻微声响。走了大概几十米远,我心里那种毛毛的感觉又来了,
忍不住停下脚步,猛地回头朝身后望去——这一望,差点把我的魂儿都给吓飞了!那个哑童,
他竟然还跟在我后面!距离我只有短短几步远,依旧是那副呆呆愣愣的样子,
直勾勾地看着我,那双玻璃球似的眼睛,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下,显得更加明亮,也更加空洞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还跟着我?”我停下脚步,心脏“咚咚咚”地擂鼓,
声音因为害怕而有些发颤,“你不回家吗?天都快黑了!你家到底在哪儿啊?
”他像是根本没听见我的问话,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,目光牢牢地锁定在我身上。
他的嘴唇微微翕动了一下,似乎想说什么,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,
只有一股带着河底淤泥特有的、腥冷潮湿的气息,随着他嘴唇的动作飘了过来,
钻进我的鼻孔,让我胃里一阵翻腾,差点吐出来。“你说话啊!”我又惊又怕,
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八度,“你爸妈呢?天黑了他们不找你吗?你快回家去!
”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他就那么僵直地站着,像是一尊被遗忘在路边的泥塑雕像,
脸上没有任何属于活人的表情波动。可是那双眼睛,却死死地、固执地黏在我身上,
那眼神深处空洞无比,却又好像带着一种莫名的吸力,让我感到一阵阵心悸。天色暗得很快,
乡下的傍晚就是这样,太阳一落山,光亮就像被什么东西迅速吸走了一样。四周越来越暗,
风也更大了,吹得两旁的玉米叶子“哗啦啦”响成一片,那声音听起来,
简直就像有无数只冰凉的手,在玉米地里穿梭,马上就要伸出来抓住我的脚踝。
我看着他那张在暮色中愈发显得青白诡异的脸,心里的恐惧像野草一样疯长,
一个荒谬却又无比清晰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:他不是人!他绝对不是活人!
“你别跟着我了!滚开!”极度的恐惧瞬间冲垮了我的理智,我脑子里一片空白,
只剩下一个念头——让他消失!让他离我远点!鬼使神差地,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,
或许是恐惧到了极点转化成了愤怒,我突然往前猛冲了一步,伸出双手,用尽全身力气,
狠狠地朝他胸口推了过去!他似乎完全没有防备,或者说,他根本就没想过要躲闪。
被我这么一推,他“扑通”一声,直挺挺地向后摔倒在坚硬的泥路上,
身上那件粗布褂子沾上了更多的泥土和灰尘。可即便如此,他依旧没有哭,没有喊,
甚至连一声吃痛的闷哼都没有。他就那么仰面朝天地摔在地上,
然后慢慢地、用一种极其僵硬诡异的姿势,抬起头,脖颈仿佛缺乏润滑的轴承,
发出细微的“咔哒”声,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,依旧直勾勾地看向我,
眼神里没有预料中的委屈,也没有被攻击后的愤怒,只有一片死寂的、深不见底的虚无。
但在那虚无的最深处,我好像……又看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、类似于恳求的东西?
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,他摔倒的那片泥地上,竟然以他的身体为中心,
快速地渗出了一小滩颜色发黑、粘稠浑浊的液体!
那液体带着一股极其浓烈、令人作呕的腥臭气,
就像是河底沉积了多年的、混杂着腐烂水草的淤泥被翻搅了上来!
我吓得三魂七魄丢了一大半,哪里还敢再多看一眼,转身就没命地朝着大伯家的方向狂奔,
耳边只剩下自己粗重的喘息声、擂鼓般的心跳声,
以及……身后似乎隐隐约约传来的一阵轻微的、黏糊糊的“沙沙”声,那声音不像是脚步声,
倒更像是什么东西在泥地里一下下地、艰难地爬行……我一路不敢回头,
拼尽全力跑回大伯家,“砰”地一声撞开院门,踉踉跄跄地冲了进去。
爸妈和大伯大妈正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说着话,
看到我脸色煞白、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的狼狈样子,我妈连忙站起身迎过来,
关切地问:“怎么了这是?跑这么急,后面有狗追你啊?
看你这一头汗……”“妈……妈……”我一把抓住我妈的手,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
手心里全是冰凉的冷汗,说话都带着颤音,
…我……我推了他一把……他……他摔在地上……流……流出来的不是血……是……是黑水!
又黑又腥的黑水!”“小孩?”大伯闻言皱紧了眉头,放下手里的茶杯,神色严肃起来,
“哪个小孩?长啥样?是咱们村的吗?”“不……不是,我不认识,”我惊魂未定地摇着头,
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
一股河底的泥腥味……太阳那么晒他也不流汗……我……我推倒他……他就渗出来一滩黑水!
就在回来的路上!”大伯和大妈对视了一眼,两人的脸色几乎同时变了。
大妈不自觉地抓紧了自己的衣角,声音也有些发紧:“不对啊……咱们村就这么大点儿,
谁家有娃,多大年纪,我都清清楚楚……最近也没听说谁家有亲戚娃来串门子。而且这几年,
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跑着打工去了,留在村里的娃娃更少了,就那么几个,都在东头玩,
哪儿来的这么个哑巴娃?还……还渗黑水?”“会不会是邻村跑过来玩的?
”我爸也察觉到事情不简单,语气凝重地插话问道。“邻村?”大伯站起身,
眉头锁得更紧了,脸色沉得像是要滴出水来,“邻村跟咱们村就隔着那条河,谁家有娃,
啥情况,我大致也清楚,
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个特征的哑巴娃……更别说……渗黑水这种邪乎事了……”我越听越害怕,
浑身止不住地发抖,紧紧缩在我妈怀里,声音带着哭腔:“可是我真的看到他了!
他就跟在我后面,看着我,一动不动的,身上凉得吓死人,真的没有脚印!我没骗你们!
”“别是傍晚光线暗,你看花眼了吧?”我妈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,试图安慰我,
但我能感觉到,她自己的手也有些冰凉。“我没看错!”我急得眼泪终于掉了下来,
“他就站在那里,眼神直勾勾的,可吓人了!我还推了他!那黑水……那腥味……都是真的!
”大伯看我吓得厉害,不像是在说谎或者夸大其词,他转身走进屋里,
很快拿出来一把平时下地用的锄头和一支老式的手电筒,对我爸说:“走,兄弟,
咱们一起去看看!孩子说的那条路……以前就不太干净,别是真撞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!
”我爸立刻点头同意,两个人一个拿着锄头,一个打着手电筒,沿着我刚才跑回来的路,
朝着村东头那边走去。我和我妈、大妈则留在院子里,忐忑不安地等着。
院子里的老槐树被夜风吹得枝叶摇曳,发出持续的“沙沙”声,那声音此刻听起来格外刺耳,
像是无数个声音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窃窃私语,议论着刚才发生的诡异事情。
我紧紧攥着我妈的衣角,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,眼睛死死地盯着院门的方向,
总觉得下一秒,那个哑童就会悄无声息地从门缝或者墙角的阴影里钻出来。
时间过得异常缓慢,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过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,
院门外终于传来了脚步声,大伯和我爸回来了。借着手电筒的余光,我能清楚地看到,
他们两个人的脸色都异常难看,是一种混杂着惊疑和紧张的苍白。
他们手里拿着的锄头和手电筒上都沾了些新鲜的泥点,我爸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冷汗,
连头发都有些湿漉漉地贴在皮肤上。“怎么样?看到人了吗?找到那孩子没有?
”大妈迫不及待地迎上去问道,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尖锐。大伯摇了摇头,
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,似乎咽了口唾沫,沉默了好几秒钟,
才嗓音有些干涩地开口:“没……没人。从咱们家門口到东头田埂那一路上,
我们都仔细看过了,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……田埂上只有咱家娃跑回来时留下的那一串脚印,
还有……”“还有什么?”我妈紧跟着追问,手不自觉地搂紧了我的肩膀。
“还有一滩……黑水,”我爸接过话,语气沉重得像是压了块石头,
“就在娃说推倒那东西的地方,地上确实有一滩颜色发黑、粘稠稠的泥水,腥气扑鼻,
就是那种河底淤泥的臭味……而且,
在那滩黑水旁边……我们还看到了几个……小小的手印……”“手印?”我心里一紧。“嗯,
”我爸点了点头,脸色更加难看,“像是小孩的手印,
很小……但是……那手印的样子很奇怪……不是按在泥表面的,
而是……而是像是从泥地底下,硬生生往上按出来的!每个手指头的轮廓都深深嵌在泥里,
边缘清晰得吓人!”我吓得浑身血液都快要凝固了,手脚一片冰凉。嵌在泥地里的手印?
从底下往上按出来的?那……那得是什么东西,才能从泥土下面伸出手来留下印记?
难道……难道那个哑童,根本就不是走在路上,而是……一直埋在路下的泥土里跟着我?
这个念头让我如坠冰窟,牙齿都开始不受控制地打颤。“别瞎琢磨了!赶紧都进屋去!
天黑了,外面不安全,都别待在外面了!”大伯语气严厉地说道,他把锄头靠在院墙角落,
脸色依旧铁青,看不到一丝血色,“把门窗都检查一遍,锁死!今晚谁也别出这个院子!
”那天的晚饭,我一口都没吃下去,毫无胃口。
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那个哑童直勾勾的眼神、青白色的脸、走路无声的样子,
还有那滩腥臭的黑水以及爸爸描述的、从泥底下按上来的手印。
一个个问题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旋转,让我坐立难安,
总觉得暗处有一双冰冷的、没有感情的眼睛,在时刻不停地盯着我,无论我躲在哪个角落,
那道视线都能穿透墙壁,落在我身上。夜里,我睡得极其不踏实,噩梦一个接着一个。
到了后半夜,突然被一阵轰隆隆的炸雷声惊醒了。窗外电闪雷鸣,狂风呼啸,
把窗户吹得“哐哐”作响,紧接着,瓢泼大雨就砸了下来,
豆大的雨点密集地敲打在屋顶的瓦片上、窗户的玻璃上,发出噼里啪啦的巨响,
那声音猛烈得像是无数颗小石子从天而降,要把房子彻底砸穿。
我从小就害怕这种雷雨交加的夜晚,此刻更是吓得缩成一团,赶紧钻进被窝里,
用被子把自己连头带脚蒙得严严实实。可即便如此,
那震耳欲聋的雷声还是能穿透厚厚的棉被,一下下撞击着我的耳膜,仿佛就在屋顶上炸开。
而且,在隆隆的雷声和哗哗的雨声间隙,
我好像还听到了一种别的、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——一种“窸窸窣窣”的,
像是有人用长长的、坚硬的指甲,在一下下反复刮擦窗户玻璃的声音!
我在被窝里憋得满头大汗,几乎要喘不过气,但又不敢把头露出去。过了不知道多久,
实在忍不住了,我才战战兢兢地、极其缓慢地把被子掀开一条小缝,只露出一只眼睛,
惊恐地望向窗户的方向。就在这时,一道极其刺眼的闪电猛地划破夜空,
如同一条银白色的巨蟒,瞬间将天地照得一片惨白,也清晰地照亮了我家院子的每一个角落。